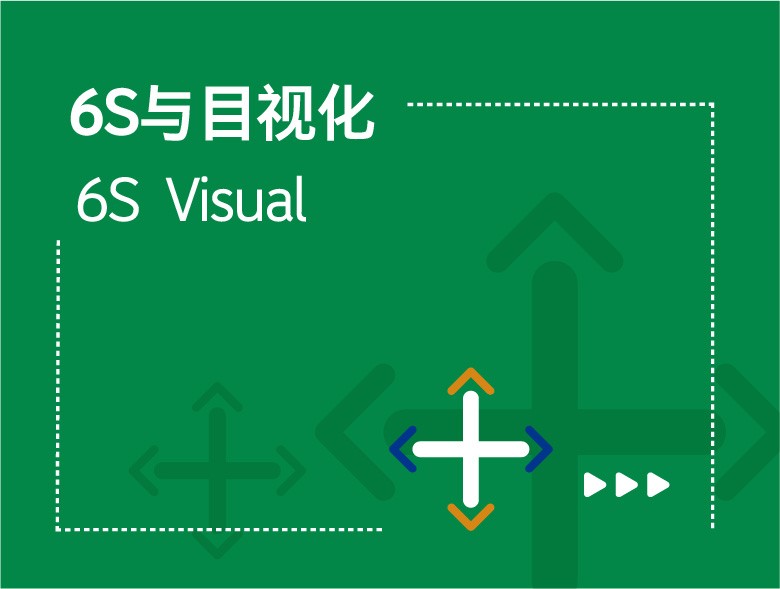相關推薦
亨利·福特是世界上第一個對精益有系統性認識的人,他非常關注創造價值的過程,而不僅僅關注公司的資產和組織架構。他也是第一個對價值流從開始到結束有深刻理解的人,包括產品概念的誕生到投產、原材料采購到客戶服務等。此外,福特更是歷史上有名的對浪費“疾惡如仇”的人。有人會說豐田的大野耐一比老福特更甚,但是大野耐一卻一再告訴大家,他是通過閱讀福特的書籍才學會如何改進的。
老福特強調先去觀察分析每個步驟,判斷其是否創造價值,然后再采取行動,把不能創造價值的步驟消除掉!(這是老福特批評弗雷迪里克·泰勒和科學管理法最經典的一段:“為什么要求員工更努力地工作,去完成一些不必要的工作?有些步驟可能經過正確的流程安排或生產布局,就可以免除了!”)當我們把不能創造價值的步驟都消除后,剩下的就構成了“連續流”。
1914年,老福特在高地公園把T型車的生產流程都安排在一棟廠房中,其中,許多流程幾乎達到連續流的要求。他們使用單元生產方式來生產零配件,以輔助整車的流水線,并在流水線設置“缺貨”的偵察員,在每個裝配點監測庫存并將信息反饋到上游工序,創造了早期的拉動系統。這種作法可以按照下游工序的需要,靈活地調節上游的生產速度。
同樣令人驚嘆的是,老福特將工程師安排在一個大房間里,由他直接領導。僅用了3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T型車的設計,這是精益歷史上的一個亮點。

亨利·福特在高地公園工廠負責的管理面很廣,因為他對一切都太熟悉了,隨時都能掌握設計、生產和裝配的狀況。他并沒有培養干部去觀察浪費并消除浪費,他也從不需要衡量指標。
這種個人管理的模式,隨著公司的成長逐漸變得不切實際。但老福特也不知道該用什么方法來取代自己慣用的管理方法。他能做的就是使用更多的自動傳送帶,把每個步驟連接起來,就像1920年胭脂河的工廠一樣。到了1930年,整個福特公司就像是一條冗長的流水線。(大野耐一意識到傳送帶和中央生產控制是一個推動式而不是拉動式的生產系統,但那是很久之后的事了。)這是否意味著,亨利·福特以為公司只需要有他本人就能搞定,而當時福特公司已經成長為全球最大的制造企業?
1930年,當福特試圖在同一產線上生產多種不同車型來滿足多變的市場需求時,這套管理系統終于崩潰了。福特公司憑借T型車累積的財富繼續前進,直到1945年,亨利·福特的孫子——福特二世接管公司,才又開始了一個新的紀元。
福特二世面對當時的情況,努力地去尋找一個新的管理模式。他閱讀了彼得·德魯克1946年的經典著作《公司的概念》非常認同通用汽車的管理模式,于是迅速地把福特公司改變成另一個通用。
這是一個巨大的改變。老福特非常重視現場,常到生產線上觀察創造價值的過程;而通用汽車公司主要依靠分析財務數據來管理,比如資產利用率(和銷售量比較)、庫存周期、不良品成本以及工程師的數目等。經理通過完成由公司總部幕僚訂出的指標來獲得獎勵,但可惜的是,這些幕僚并不理解公司的實際運作。他們認為大批量生產是提高機器利用率、降低單件成本的最好方法,把老福特最重視的點到點的價值流放置一旁。
福特公司的領導層很快采用了愛德華·蘭迪(J. Edward Lundy)設計的財務管理方式。某種程度上,它比通用的管理方式更嚴格、更有控制力。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和“神童隊”(Whiz Kids)都是很典型的代表人物。福特二世沿用通用汽車的方法,重新贏得了競爭力,穩坐世界汽車業的第二把交椅。
20世紀40年代后期,福特、通用和克萊斯勒成為在同一城市、使用同樣管理模式、有著相同工會的三大汽車公司。由于進入汽車行業的門檻很高,汽車行業出現了長達40年的穩定期,直至20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汽車進軍北美,才打破這個局面。
當大家發現日本的豐田和本田汽車公司使用一種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時,福特公司一時間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丹尼爾·瓊斯、丹尼爾·魯斯和我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合著《改變世界的機器》,我們曾記載美國福特公司應用精益的方法管理生產線,已經大大提高產能的例子。我們想證明的是,至少有一家美國汽車公司已經應用精益思想,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我們不能評論福特當前的管理系統,因為沒有到實地去做研究。但我們知道福特公司的管理層還是繼續依據財務數據來管理,已經遺忘了老福特的現場管理。更糟的是福特的產品開發和供應商管理系統沒有任何創新的改變。
福特公司通過大型皮卡和SUV,在本土市場保持了20年的成功。這些都是美國產品,適用于路面寬闊、油價低廉的美國。除非日本公司愿意設計類似的汽車并在美國投資生產,才有可能對福特的市場份額有威脅。
在1997年,我接到當時負責福特北美業務、正邁向CEO 寶座的杰克·納賽爾(Jack Nasser)的電話。他告訴我,探索者和F100皮卡系列是福特僅存的盈利產品,他估計福特公司只有4年的準備時間來和豐田做正面的競爭。他擔心日本汽車公司會以較低的成本生產更好質量的大型皮卡和SUV,進而打擊福特的市場。他問:“福特怎么才能在4年內,變成另一個豐田呢?”
我們就這個問題促膝長談,我認為解決的方法是從根本上改變供應商管理系統、產品設計系統、生產管理系統,以及企業運作管理系統。他立刻總結說“這太難了”。于是,他轉而改變了管理指標,開除表現不佳的員工,并嘗試網絡銷售汽車!他沒有再和我聯系,我也沒有興趣再繼續這段談話。
福特在納賽爾的管理模式下,又維持了5年,最終還是逃不過預期的危機。我對福特的新任CEO艾倫·穆拉利(Alan Mulally),還是保持同樣的建議,系統性地重整供應商的管理系統、產品開發系統,從接到訂單到購買材料到加工成形的生產流程,并重點關注信息的管理系統。(福特可以從他們與馬自達的合資工廠繼續學習,馬自達在1973年的危機后,已經成為一個很好的豐田學生。)

福特公司必須系統性地思考管理層的職責以及執行的方式,重新拾起老福特現場管理的原則。福特在這場浴火重生、重新定義出發的過程中,應該主動向豐田學習,找回他們早先教給豐田的那一套管理體系。
此外,福特還需要重新思考對員工的承諾和關系,因為福特公司只是全球市場中一個普通城市(不再僅有一個工會)的普通企業(不是壟斷經營者)。最后,重新思考品牌策略,撤銷不盈利的產品——水星、捷豹、林肯?關注用戶有需求的主要品牌,在不同的價位上,提供性能優良、高質量的汽車。(請注意:要從客戶長期伙伴的角度,而不僅是一次性買賣的位置來思考公司產品和顧客要求的差距。)
誰也不知道以上這些建議是否有效,但卻是一條自我救贖的精益之道。如果管理層不能迅速地采取行動,從福特的早期學生(豐田)那里學習精益管理,而最終導致企業崩潰,那將是一場悲劇。
文章來自網絡,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掃描進入小程序
掃描進入小程序